跳跃式更新写。因为也跳跃式翻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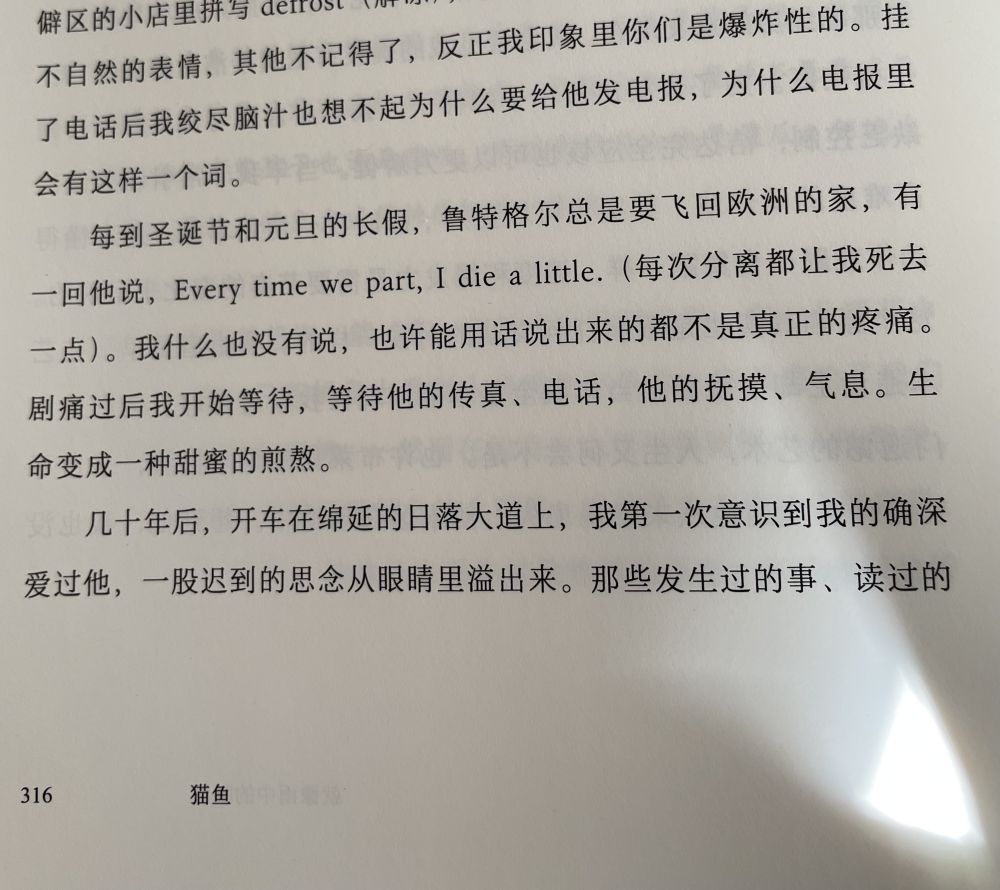
读到书里这句英文,想到钱德勒的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(The Long Goodbye)。阅读的体验来自个体的认知。
《猫鱼》定价168元,下面提及陈丹青两本定价28元、48元。
小桌上堆着几本,莎士比亚英文全集,日记、圣经中英、一本牛津大学版美国诗集,一只皮小包,再有两本陈丹青的《多余的素材》、《纽约琐记》(都是修订版,2010年回上海买)。
前两天翻出陈丹青的书,想,要不要断舍离。又觉得可以留,他是六十一中学校友,即民立中学。翻到书里提及他写到中学名字与班主任那两页,拍照片给两位老学生,一位在德州,一位在上海。她们都不知道。
陈冲也提及陈丹青,在写到陈川的篇幅。陈丹青画过陈冲。
终于找到了我想对照读的内容。陈丹青《纽约琐记》,294页“二十年前,'文革'后第一次大型外国美展'法国乡村绘画'来沪。”陈丹青没有写展馆在哪里。写作上,他当年下笔仍然有知青腔,纹身般。陈冲写到了,“'文革'后上海的第一个西方艺术展览,是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的'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',展品都是法国卢浮宫与奥赛博物馆的名作,展馆内外如饥似渴的人群如浪潮一般。”
为什么展名都有所不同,按我推测,陈冲的更准确,陈丹青的大概是脑海里的印记。回忆不一定准确。“农村”好像更符合那个年代的宣传风格。
这就是读书的乐趣,多读一本书可以多确认一下,避免片面与偏激。
陈川的文字比陈冲的更细腻,印象,耐读。与陈丹青比,陈川是上海的,没有一点泥痕与知青后遗症(我加上的名)。陈川没有离开上海下乡过。时代就是那样,反弹在个人身上,连文字都有气味。
网络里,有评论一天就读完了《猫鱼》。这是一本可以快餐般下咽的书吗?我在太阳房开了一盏台灯,继续读。龄走过来,是她带回来的灯,说放这里蛮好。
我想这本书,大约是陈冲年纪的,与上医有关的读者读起来最亲近了。忽然想到,疫情前的秋天,去本地婚宴,与一位上医毕业的七十多岁女士交流两句,六六年,她在上医目睹过颜福庆被批斗。书里出现颜福庆名字,下面没有注释,年轻的一代读者怎么会知道?
与上海做编辑的老友微信,指出我发现陈冲的书里一个错。她回复,我是对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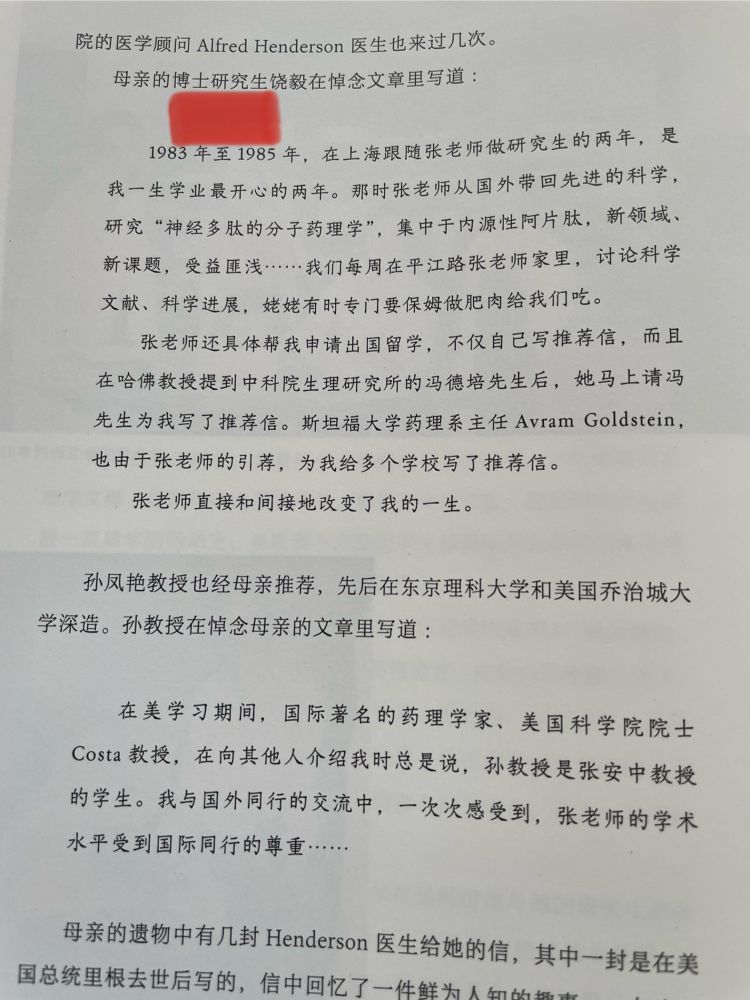
陈冲写“博士研究生”错,饶毅是她妈妈硕士研究生。

厨师长带回来的行李箱打开,很乱,不知道每个塑料袋里装了什么。逃难一样。去年他才独立整理行李箱。你能够期望什么呢?善待自己,就是睁一眼闭一眼。
龄的行李箱被打开后也是井井有条,叫我想到高中数学的集合概念。有静物画之感,甚至不愿取出物品。
一袋零食,怎么买的?与袜子店老板聊天,一个青年经过,推着小车兜售。来自黑龙江的大三学生勤工俭学。自然要买一袋。厨师长叙述。忽然对比了我之前写的想卖中文书。暗自赞了厨师长与我都会有此心。比如薇薇安第一次说卖我一只二手小包,我连价都不还。这才有友情的开始。信任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就是磨练的过程。
周五下午厨师长到家。我做了韭菜虾仁猪肉饺子。洗碗之后去邻居家加个小班。Addy小姑娘哭都稀里哗啦,不愿爸爸离开。但真一走,她累了,躺沙发,一刻钟后熟睡。我读了至少两个半小时书。她家的猫斯蒂夫在我的另一边。猫知道我是爱猫人士。
我便读《猫鱼》。网络里读过其中的二三篇。当时读,不知道平江路,虽然想,肯定看见过路牌。真想不起来。等到书里写到枫林桥,上医。啊!想起来了,1993年秋天,我不是乘43路在枫林桥站下,沿着枫林路走到斜土路吗?泰康食品厂的万年青饼干的香味好像也回来了。我是去师大同学逸凡家。那时我们大一。我应该见到了平江路路牌。
本来今天有读书会活动。没有去,在太阳房读读书,晒太阳,Coco也是。外公昨天回来,Coco比较有经验了。很乖很乖的猫。
陈冲写的很好。随便翻一页,用到狄金森诗,或里尔克或斯坦贝克,知道她的阅读宽度了。她的文字厚度是家传的素养。
可以不谈收养事件吗?我读时,只看文字。Judge他人,是上帝的事。
难得有一本想读的中文书,还是有上海。高中同学替我下单买,快递到婆婆家。厨师长下楼取。厨师长也开读了。
厨师长在上海去了两个美术展馆,一个是看贝大师的“人生如建筑”。……
人生到底如什么?
陈冲用小菜场最便宜的“猫鱼”注释。我的大表姐很像陈冲,差不多年纪。也是很早年纪会去小菜场买菜,顺便买油条大饼。
有时读书是换回一点记忆。书是必须的零食,多读才能写好。
我喜欢这样静心的时候,既能读书,还能赚点零花钱。很是幸福。
陈冲的《猫鱼》(更新着)
觉晓 发表评论于
谢谢文心。他的文字里很深的时代印痕。他中学和原来的家,乃至小学所在,是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图。
最近看过一点他的视频,厨师长找的,他也是老人了,终于眼光里柔和起来。
他的父母都被打成右派,学校里很难抬起头。
最近看过一点他的视频,厨师长找的,他也是老人了,终于眼光里柔和起来。
他的父母都被打成右派,学校里很难抬起头。
浮世文心 发表评论于
对陈丹青印像不好。记得有一次读他一篇文章说贝多芬、莫扎特都是同性恋,论据是他们都没有结婚。觉得这人也太自大,如此信口开河。总的来说,觉得下乡知青多半有痞子气。
觉晓 发表评论于
谢谢真凡。夫妻是彼此照顾。有的人从小被母亲照顾到“断手断脚”。:)
陈冲哥哥陈川的文字更耐读,画家的眼光,连阴沟边的蒲公英黄花都看见了,哎,很狄金森诗意。
陈冲哥哥陈川的文字更耐读,画家的眼光,连阴沟边的蒲公英黄花都看见了,哎,很狄金森诗意。
FrankTruce1 发表评论于
哈哈,你先生平常出行该是被你照顾得很好了:)
关于陈冲,有段时间正好先后看了她演的《红玫瑰白玫瑰》和《色戒》的两个角色,演技都很在线,很佩服!
另外,关于《猫鱼》的书名,让我想起了乔布斯的大女儿,一直得不到乔布斯的关爱,她写的自传名字也叫小鱼《small fry),这本书被许多评论家认为写得诚恳而深刻,算是让人看到了商界奇才的不为广知的一面。
关于陈冲,有段时间正好先后看了她演的《红玫瑰白玫瑰》和《色戒》的两个角色,演技都很在线,很佩服!
另外,关于《猫鱼》的书名,让我想起了乔布斯的大女儿,一直得不到乔布斯的关爱,她写的自传名字也叫小鱼《small fry),这本书被许多评论家认为写得诚恳而深刻,算是让人看到了商界奇才的不为广知的一面。
登录后才可评论.